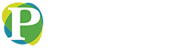演员朱琳66岁了,然而现实中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实在年轻许多。
作为86版《西游记》里最出彩的一笔,端庄又娇羞的朱琳,是无数观众心中永远的“女儿国国王”,“悄悄问圣僧,女儿美不美”的旋律响起,还是能让人心尖微颤。
不管走到哪,女儿国国王都是朱琳甩不开的话题和标签,但她并不因此苦恼,直言,“一个人一辈子演无数角色,大家能记住一个经典形象就不错了。”
朱琳因影视出名,然而退休之后的她,早已转型舞台剧和有声小说领域。今年9月,朱琳便将带着文学朗读音乐剧场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,登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。
86版《西游记》女儿国国王
朗诵对话大提琴
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是茨威格最著名的短篇小说,讲了这样一个爱情故事:男主人公在四十一岁生日这天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,写信之人是一个将死的、偷偷爱了他十八年的女子,初遇这个男人的瞬间,她便坠入情网,之后,她走过了孩童时的懵懂爱慕,经历了世俗的洗礼,直到临死前写这封信,唯一没变过的就是她的爱,而他却对这一切毫不知情。
这还是朱琳第一次以纯文学朗读和现场音乐结合的形式,演绎世界经典。
“看欧洲大文豪的作品是我们那个年代唯一的文学享受。”朱琳回忆,自己最开始接触茨威格是改革开放以后,家里有一本茨威格小说选,张玉书翻译的,他的语言文字有原作者风格,也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习惯,朱琳这次朗诵的便是他的版本。
不再拍影视后,朱琳登台演绎的都是自己真正心仪的经典。在此之前,她扮演过姿态各异的女性,如今退休了,她对女性的探索没停止。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可以说和她心灵相通。
朱琳近期照片
茨威格常常从男性的角度描绘女性独特隐秘的情感世界,他笔下的人物往往细腻、敏感甚至神经质,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就像一个女人的内心独白,给了演员很大的展示空间。
“他擅长观察成人世界的情欲表达,善于描绘被情欲主宰的人,而我们要回归文学作品最原始的状态。影视有很多外在的表现手段,一旦回归文本,技巧就不存在了,你调动的是你这些年的所思所想、情感体验。这是我喜欢的,也是我这些年做演员的长项。”
在朱琳看来,茨威格的笔就像“手术刀”,在剖析和挖掘女性的世界时,力道细腻、精准,读者想知道什么,他的笔就写到哪儿,“他都写出来了,而我就一个小时的朗读时间。他用小刀一点点拉开来让你看,可能温情可能血淋淋,都在考验我的功力。”
演出时,和朱琳一同登台的还有法国大提琴家索尼娅·维德-安瑟顿。除了和名团合作,索尼娅这些年也在积极拓宽表演形式,她和女演员夏洛特·兰普林合演过《夜舞曲》,也和法国影星芬妮·阿尔丹合作过《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夜船》朗读音乐会。
朱琳和索尼娅尚未见过面,但两人已经传阅过彼此的演出视频和录音。
在朱琳眼里,大提琴是中性的乐器,既可以男性又可以女性,既能倾诉、抒发、宣泄,又能倾听,角色的转换是自如的。而索尼娅的演奏在她眼里也是中性的,琴声里有细腻也有粗犷,给人力量感和冲击力。
朱琳感慨,过去在国内,音乐往往沦为伴奏和背景,很少作为独立形象出现,很多高大上的演出请了作曲家写大型交响乐,最后,交响乐不是变成伴奏就是抢演员的戏,二者很少有平等的关系。
“我们首先是一种对话,和性别的撞击。”朱琳将大提琴当成倾诉的对象,她希望二人上台时,观众不是只盯着自己看,把大提琴当成背景音乐,“她的琴声会引领我,和我对话,她会倾听我的诉说、苦痛、哀怨、喜悦,她首先应该接受到,再用琴声表达出来,这才是两种艺术符号有机的结合。”
同样是朗读经典名著,去年6月,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·于佩尔来华朗读杜拉斯的《情人》,曾在业内外引起广泛关注。
在北京,朱琳特意去看了于佩尔的演出。她和时下的年轻人一样喊她于老师,“于老师在台上真的有一种少女的娇羞,她是从13岁少女开始演的,我不行,我是很有分量的‘王者风范’,但我也要从年轻女性的感受入手。”
朱琳坦诚,因为忙着看字幕,前十几分钟她并没有看进去,看到四分之一,她瞬间被打动了,少女后来坐船离开越南回法国,也让她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
那台演出的舞美也让她印象深刻,一棵椰子树的剪影就是越南,一台风扇代表了燥热,舞美的简洁让人忘记了技术手段的存在。在舞美上做减法,在这一点上,朱琳和于佩尔的想法是相通的。
朱琳反对舞台给观众强加东西,淋漓尽致地告诉他们这是什么年代、什么背景,“这些外部的东西会影响观众的欣赏,尤其是文学青年非常敏感,他们对文学信息的捕捉有自己的习惯和渠道,所以绝对不能强加观众。”
朱琳早年照片
本色出演女儿国国王
按现在流行的说法,朱琳是扎扎实实的文艺女青年。从小,她就爱好文艺。1969年,朱琳考入北京部队通讯兵文工团当舞蹈演员,1975年转业到北京一家研究所当化学分析员。
朱琳和影视圈结缘于1980年。当时,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了电影《叛国者》专门到北京选演员,朱琳被选中饰演动物学家的助手。
“我当时在研究所实习,他们找到我,觉得我的身份、经历、专业和电影里的沈虹非常吻合,就把我叫到北影厂去试戏,试了一场无实物表演的织毛衣,被选上了。”
朱琳就这样去了云南拍戏,一拍8个月,回来遇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业余培训班招生,她去应考,和赵宝刚、李成儒等成了同学。5个月后结业,朱琳被分到峨眉电影制片厂,从此走上影视之路。
温婉、端庄、大气,朱琳在银幕上的形象符合当时的国人对传统女性的审美,找上门的也基本都是知识分子、医生、工程师之类的角色。
86版《西游记》里的女儿国国王,是朱琳演艺生涯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问她当初是怎么被选上的,朱琳大笑了起来,“好看呗,像国王呗,端庄,秀丽,内心纯净,没见过男人,我觉得我都演出来了。”
拍了整整一个月,剧组才拍完《取经女儿国》这一集。既有端庄的一面,又有娇羞的一面,朱琳可以说是本色出演了女儿国国王。
在影视圈里,朱琳出了名的低调,也是出了名的乖女孩,这大概也是导演杨洁当时看中她的原因,“女儿国国王不是说就是我这样,而是我化妆定造型之后,大家以我作为一个标准。”
拍摄时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幕后故事呢?朱琳避而不答,“所有幕后的故事都在镜头前的一颦一笑中表现出来了,其实没什么,都是正常合作、正常交流。”
如今不管走到哪,提到朱琳,女儿国国王都是她甩不开的话题和标签,然而她并不把标签当成难耐的束缚。
“一个人一辈子演无数角色,大家记住的应该是最经典的几个。” 朱琳笑说,这样一部根据名著改编的经典,这么多反复在寒暑假播出,一代又一代观众收看,就给它加分了,“后面也出了无数版本,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解读,不同创作者有不同的理解,都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们那一版的审美在这样一个高度,很难超过,所以大家能记住一个经典形象就不错了。”
闲暇爱看小说听歌剧
从影三十多年,朱琳最近一部播出的电视剧,定格在《重案六组4》(2011)。
她在戏里演一个私人会所女老板,亦正亦邪,挑战起来十分过瘾,“这样的人往往被写得很世俗,层次不高,其实恰恰不是,真正生活中,这样的女性可以很自如,她有慈母的面容、蛇蝎的心肠,是可以挖掘的。”
朱琳感概,如今影视剧里的中年女性角色都容易写得不正常,“这个角色的分寸感把握比较好,和生活距离不远,不是那么戏剧性。现在的中国影视太假了,提炼得过多,人的情感没有细节。”
演绎角色时,朱琳追求对人性的挖掘,这也是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让她着迷的原因。
“这部作品讲的是人性,很多中国作品为什么没有人性?它有故事、有矛盾、有冲突、有起承转合,但恰恰没有人性,剧中故事就像你家发生的事,她们就像是你身边的人,妈、婆婆、岳母……但没有东西可挖,就一张白纸在内。”
这或许也是朱琳不再频繁拍戏的原因。到了一定年龄,家庭剧和婆媳剧似乎是女演员的必然归宿,然而朱琳自觉不合适。
在她看来,家庭剧里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符号,“每次接戏,每演一个人物,我都会问她是干什么的。如果退休了,她退休前是做什么的,老师、医生还是干部?她的细节和行为举止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这个角色只是一个妈妈,我就看不见摸不着了,不知道往哪里努力了,就没有深度、没有个性、没什么价值。”
除了演舞台剧,在电台录“有声小说”如今也占了朱琳很大一部分精力,《歌剧魅影》《乔家的儿女》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都是她的代表作。
“你无法借住形象去表现人物,唯一可以运用的表演工具就是声音,播音员一辈子靠声音塑造形形色色的形象,这是一个功夫。”比如狄更斯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,“作者深层次想表达的内容都在字里行间,影视改编只是节选可视性的东西。你要慢慢去理解,反复阅读。通过电波,读者和听众有一种互动,这种东西可能只有听广播的人才能感受到。”
最近,配音综艺《声临其境》大火,不过在朱琳看来,节目无法完全还原配音演员的创作过程,“他们拿出来的都是最有意思的段落,可是在话筒前录小说,是一个让心静下来的过程,有意思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,回到文学本身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
闲暇时,朱琳就在家看小说,最近正在读美国作家阿图·葛文德的《医生三部曲:最好的告别》。作为一名资深文青,朱琳是看小说长大的。青年时期,欣赏文学作品是他们那一代人最大的娱乐,欧洲大文豪带来的艺术滋养和熏陶,对朱琳成为演员也是必不可少的助力。
朱琳也爱听古典音乐,尤其是歌剧。歌剧里音乐性和戏剧性的结合让她迷恋。
她迷恋的作曲家,通俗一点的有普契尼,《蝴蝶夫人》是她喜欢的,口味重一点的有瓦格纳,有人嫌瓦格纳的歌剧沉闷、难懂、篇幅长还不中场休息,朱琳却很迷恋他歌剧里的人文色彩、人性思考和哲学思维。
在北京,朱琳时不时就会出门看演出,但更多时候,她选择在家看碟,“到了这个年龄,我看东西对娱乐性和趣味性的追求就比较低了,我会经常问为什么,问自己为什么,问创作者为什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