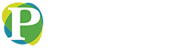沈阳啊沈阳
沈阳啊沈阳
第一次来沈阳,大概在四十几年前,那时我还是个农村娃娃,没上学,也许刚刚能数得上一百个数,我们那里入学的标准就是能数出从一到一百的数字。爸爸平时里对我的训练就是从数数开始,他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孩子,但那时大人们对于孩子们的管教都是听话为主,学习上的事,大多是听之任之,有关心孩子的家长,不过是孩子成绩好的时候给几句表扬,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给几句诅咒甚至痛哭几句,当然也有挨巴掌和被踢的孩子,那就要看运气好坏了。

我能在上学前去一趟沈阳,现在来看,是爸爸对我的启蒙教育。我们家在一个小山村,山不算高,有一条小河穿村而过,有一条沙石路伴河而行,也是穿村而过。这是一个闭塞的小山村,人们所有的足迹都留在小路上和小河里。
爸爸是少数几个从大队到公社当临时工人的生产队员,这里面自然有许多曲折的故事,自然是颇费了一番努力,从小队到大队、从大队到公社,从种地到开手扶拖拉机,从开手扶拖拉机到做一位铸造厂的工人,那时在整个生产大队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。

爸爸在公社的工厂里干得也算不错,后来还有了出公差的机会,先是从公社到县城,再从县城到市里面,甚至也去过省城,也就是沈阳市。那时候爸爸最远的地方去过加各答奇,是黑龙江省的一个地名,爸爸去那里是“背”土豆种子,虽然在公社上班,家里的园田地还是要种的,土豆是家家要栽的,它既可以当粮食,也可以当蔬菜。
那时候,“吃”是天大的事,吃不饱是全大队的事。尽管爸爸在外面上班了,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吃不饱的问题,我后来才明白,那时候,吃不饱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。能吃饱的才是问题,仔细追究一下,那些吃饱的家庭,都是家里面有“国”工的,也就是月月拿工资,还有大米白面豆油白糖可以分配的国家正式工人。而爸爸仅仅是个公社工厂的临时工,还是农民的身份,比农民的待遇强不了多少。

我们那时候的主粮是包米和少量的高粱,土豆和白菜是家常菜,一年到头能见到一两次猪肉和带鱼,就是过年的时候。如果比对一下,今天的猪食可能都比我们当年的伙食要强好多吧。包米一般是做成饽饽和酸面条,土豆年年种,真正是吃不到多少的,都拿去换粮食了,白菜多数是在大铁锅里熬,有那么一点猪油花儿,偶尔也吃炒白菜,那是要多费猪油的,属于好日子,改善伙食了。
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爸爸获得了一次去沈阳出公差的机会,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“美差”这一说法,但能出去见见世面,的确让一村的人开了眼界。沈阳啊沈阳,一个村子有几个人去过呢?尤其是小孩子,听说过沈阳吗?
爸爸居然利用这次去沈阳的机会,把我从一个小山村,直接带到了沈阳,那时我没有任何对于一座省城的知识储备,我还仅仅能数上一百个数,平时只坐过牛车,艳羡过马车,见过手扶拖拉机,翻过山冈去过国营的滑石矿,那地方据说全是工人,住着成排的二层红砖楼房,据说全是吃细粮的。矿里有外贸公司的日本大汽车,喇叭很响,能把小孩的耳朵震聋半天。还有小火车,冒黑烟吐白汽儿,吼起来能把小孩震个“屁股墩儿”。
我来沈阳之前的全部非农村的知识体系就是这么多了。我不记得当年我是怎样一副德行了。穿上最好的衣服了吧,当然是补丁最少的、洗得最干净的,有没有淌鼻涕肯定是记不住的。参照一下别的孩子,大鼻涕过河是常事,袖口擦得锃亮也是常事。
爸爸居然带我去了一趟沈阳,这不是要出我的洋相吗?
到今天,我仍然记得那次沈阳之行的三件大事,我相信这会记到死的,也在很大层面上影响了我。
第一件事,就是吃。我在沈阳大概是呆了五六天。油条和豆浆是每天都要吃的东西。在那之前,我不知道油条是什么东西?豆浆是什么东西?我见过豆腐,豆腐脑儿和豆腐渣,豆腐渣常吃,但豆腐不常吃,豆腐脑儿偶尔喝过。我的肠胃显然逆反这种吃法,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。尤其是油条,油腻腻的味道,闻着就受不了,还一直吃了五六天。素食的动物,误吃了油腻,身体器官是无法承受的,它们首先不是兴奋地去适应,而是被这种“非食物”所毒害而产生各种不舒适的感觉。我哇哇地吐了很久,把几天来吃下去的所有“非食物”全部吐出来,连同肚子里面的蛔虫也一并吐出来。从此,我便与这两样东西结了冤仇,直到三十岁之后,才慢慢和解。今天,所有我过去在吃饭时讨厌甚至痛恨的食物,比如包米面、土豆、白菜、豆浆、油条,都成了我爱吃的东西。
第二件事,是去故宫。爸爸带我去那里,显然是让我大开眼界吧。一个农村的孩子,玩泥巴长起来的,故宫是什么都不清楚,又怎样开这个眼界呢?我只记得高高的墙,弯刀和弓箭。墙,我们大队有,石头砌起来的,也有泥堆出来的。刀,我们大队有,家家都有,镰刀和铡刀,那是农具啊。弓箭,我们那里没有,但我们自己可以做,用荆条和皮绳绑了,箭杆是高梁杆,弄个槐树刺针做箭头,射鸡射狗也可以笑傲江湖了。
第三件事,是对沈阳的误读。从沈阳回到农村,我俨然见过了大世面。大人们也对我刮目相看。他们喜欢问我:“你去哪啦?”我回答说:“水阳”。我把“沈”念成了“水”音。有人哈哈大笑,这些是明白人,也有一本正经的,他们也不知道对错。我去“水”阳的事,轰动了有半个月。许多人因此知道了是沈阳而不是“水”阳,但不管去没去过或者知不知道沈阳的人,见了我都爱拿这事取笑我一把。
三件小事,也许对我来说,并不很小。对于小山村的每个人来说,也不算很小。后来读《红楼梦》,刘姥姥的光荣事迹让我再回忆了一把美好的沈阳之行。今天看来,可笑的不是某个人的无知,而是群体的无知。当我们囿于某种困境而只能以苦为乐的时候,我们从来都认为这些都是合理的、天经地义的。
成年之后,多次去过沈阳,什么原因多数都不记得了。但2015年前后,去过五次沈阳,却仍然记得,都是带爸爸去沈阳的医院看病。去过沈阳医大一院和当时的陆军总医院,并且在陆军总院住过三次院,最长的一次是十四天。在这三次住院期间,爸爸一共支了十一个支架,心脏两次支架共十个、颈总动脉支了一个。十一个支架支撑着爸爸的生命,他是带着喜悦离开沈阳的,在之后的日子里,他对沈阳充满敬意,尤其对陆军总院更是视为重生之地。当时的医生说保你十年没有问题,爸爸那年是七十岁,他说能活到八十,也就值了。
人生其实很微妙,没有什么必然的因与果,一切都是自然吧。我小的时候,被爸爸带到沈阳,为了开阔我的视野。我壮年的时候,带爸爸去沈阳,为了延续他的生命。爸爸带我去故宫,我带爸爸去医院,我吃不惯沈阳的油条豆浆,爸爸在医院天天要吃高粱米水饭。
沈阳啊沈阳,这个在我们这地方仍然有许多人向往的地方,在几十年中,给了我两次终身难忘的记忆。很遗憾,爸爸并没有活到八十岁,在七十四岁那年,爸爸就离开了人世,离开了我。沈阳的医生并没有欺骗他,爸爸的心脏直到最后时刻,依然顽强。夺走他性命的是肺癌,爸爸其实对沈阳也是抱有幻想的,但肺癌没给他去沈阳的机会,其实,不仅是沈阳不会给他机会,所有的地方,也不会再给他生的机会。
从小到大,再到终老, 我们要经历许多事、见过许多人、去过许多地方,这就是生活,就是人生,就是命运。我们可能把记忆留在一个特定的地方,与它建立某种关系,产生特殊的情感。但我们无法离开一个我们不喜欢的地方,也无法永远留在一个我们喜欢的地方。我们只能说我们来过,走过,爱过,恨过,笑过,哭过。
沈阳啊沈阳,我很小的时候就去过。